因此許多作品雖出自不同藝人之手,但所鐫壺款均由一人為之,給歷代鑒賞家們帶來不少困擾。明代紫砂壺刻款字體流行楷書,多為竹刀所刻。竹刀與金屬刀刻款不同,易于鑒別。竹刀刻款泥會溢向兩邊,高出平面,留有痕跡;金屬刀刻款是在泥平面以下。
大約到明末清初開始逐漸流行印章款,據考許晉候的《六角水仙花壺》壺底有“許晉候制”篆文圓印,乃是我們所見由刻款改用印章的較早實物,此壺現藏舊金山亞洲美術博物館。不過這個時期的紫砂藝人刻款和印章還是并用的,如惠孟臣、陳鳴遠制的壺,“孟臣壺”一般是在詩詞或吉祥語章之下鐫刻“惠孟臣”三字。陳鳴遠可能是最早把書法篆刻藝術施展于壺上的第一人。他的印款渾樸蒼勁,筆法絕類褚遂良,行書款識“鳴遠”二字時人贊其有晉唐風格。“鳴壺”一般是刻款與鈐印并用,且大多是放在一起,這一特征反映由刻款向鈐印過渡時期的特點。陳曼生承襲了陳鳴遠的路子,在紫砂壺史上他首次把篆刻作為一種裝飾手段施于壺上,“曼生壺”因壺銘和篆刻而名揚四海。曼生壺的底印最常見的是“阿曼陀室”方形印,僅少數作品用“桑連理館”印。像“阿曼陀室”已是專用于曼生壺的印號。
紫砂茗壺用印多為兩方,一為底印,蓋在壺底,多為四方形姓名章;一為蓋印,用于蓋內,多為體型小的名號印。有些茗壺,在壺的把腳下也用印,稱為“腳印”。清代有不少作品有年號印,如“大清乾隆年制”一類印,還有用商號監制印的,如“吉德昌制”、“陳鼎和”等,此類印鑒民國時期頗多,這一時期款識多集中鐫于蓋上、蓋內、壺底,成為當時流行趨勢,用于壺蓋上的印章款大多是這種商號款。在壺蓋上鐫款的茗壺一般都是普通茗壺,極少有精品佳作。
紫砂壺的印章款多數為陰刻,鈐在壺上變成了陽文。但陰刻的圖章敲打在半干的泥坯上,如果用力過小,字的頂端刀痕往往難以顯露,只有用點力才可以將印章的全部刀痕打印出來。所以即使是同一印章,打印力度不同的印痕,字根相同,字尖卻是不盡相同的,這樣也常給紫砂壺印鑒款識真偽的鑒定帶來困惑。
紫砂壺用款識作偽有兩種方法,一種是真款假壺,此類大多為名家應酬或市場供不應求時,由學徒或他人代制,蓋上自己的印章。還有前代名家的印章身后流傳下來,為后人仿制冒真。另一種是假壺假款,此類作偽手法頗多。現代偽造者多是仿制假的印章或鐫刻假的款識,如采用照相制版技術,用銅鋅版制出印章。也有一些仿制者任意憑空臆造,須加辨識。紫砂壺在燒成后再補款的現象目前尚未發現。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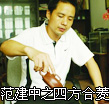

 紫砂壺名家邵順生老師
紫砂壺名家邵順生老師 紫砂壺名家之湯鳴皋
紫砂壺名家之湯鳴皋 高級工藝美術師吳芳娣
高級工藝美術師吳芳娣 高級工藝美術師錢祥芬
高級工藝美術師錢祥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