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些物質雖天然生成卻組合無序,經摔打制成泥、做坯成型后,再以1180度左右的高溫燒制成壺。此過程中,壺的色相會隨著對紫砂泥料的每次調配有所不同,也會隨著不同的窯溫和燒法有所變化,再加上泥坯燒成后的收縮率也有所不同,所以紫砂壺才得以“萬紫千紅、方非一式、圓非一相”。而配蓋又要根據原作品的品相、色相、賦意等加以調節,既要配出原作的泥、款、功,又要體現作品的形、神、氣,絕不是捏幾把砂土那么簡單的事。
1991年夏日的一個早晨,顧景舟打來電話,告知其大亨壺蓋已配好。當唐國新趕到顧景舟家中,看蓋心切的他趕緊拿起還用毛巾包裹著的“大亨壺”,掀蓋一看,上有“景舟配蓋大亨壺,時年七十有七”字樣。唐國新順勢將壺蓋與壺身合上,頓時為顧景舟精湛的紫砂技藝所折服。壺蓋不僅渾然一體,而且形、神、氣、泥、款、功都配合得天衣無縫。這把兩代紫砂壺藝大師合作的經典之作,不僅是一把壺的傳續和整合,更是兩代壺藝大師智慧和工藝的完美結合。
唐國新回憶說:“顧老自豪地說,‘除了我,誰也配不出大亨壺的豐韻、神彩、精細和豪邁,必先知其人,而后仿其壺,必先知其料,而后用其工,只有心靈和手藝的相通才能品出大亨成壺的心境,才能配出大亨作品的神韻’。顧老所表現出的激情,讓我見識了他對紫砂赤子之心般的尊敬與熱愛。”
1994年春,唐國新去上海城隍廟地攤閑逛,看見一件底有“友廷”二字的虛扁壺和一件無款的碗形直嘴壺,都沒有蓋。“也許是因為我拿壺、看壺的眼神、心態太過急切,擺地攤的又是內行,他看出了我急于購買這兩把壺,兩個壺開價8萬元,少一分不賣。”唐國新二話沒說,付了錢便提壺回家。時日不多,顧景舟趕巧出現在他家,還未落座,一眼便瞄見桌上的兩件沒蓋的紫砂壺。看罷,顧景舟頗為嗔怪:“你怎么把寶貝作煙缸?”原來,唐國新把兩把沒蓋的紫砂壺放在桌上,他朋友中多為煙民,而他自己也喜歡抽煙,無意間竟往紫砂壺中丟了許多煙蒂。唐國新一聽顧景舟此言,便趕緊將壺擦洗干凈。
此時,顧景舟感嘆道:“國新啊國新,你跟我學著看茶壺也有十幾年了,你怎么能把我親娘的公公的好東西和邵大亨的寶貝這么不當回事,居然當做煙缸,你這是暴殄天物啊……”唐國新心中犯嘀咕:“我不懂壺?我暴殄天物?這可是我東拼西湊花了8萬元買回來的,這8萬塊錢我在丁山能買一套80平方米的樓房呢。我只是再也不敢有請您配蓋的膽了!”因為唐國新知道,已近杖朝之年的顧景舟體弱多病,根本不可能再有心力重續兩代大師合奏的絕唱了。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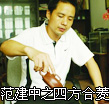

 紫砂壺名家邵順生老師
紫砂壺名家邵順生老師 紫砂壺名家之湯鳴皋
紫砂壺名家之湯鳴皋 高級工藝美術師吳芳娣
高級工藝美術師吳芳娣 高級工藝美術師錢祥芬
高級工藝美術師錢祥芬